close
試閱︱紅咖哩黃咖哩︱哪裡買
內容簡介,內容試閱,作者簡介,目錄,序,內容連載
內容簡介
她以文字構築與山相關的記憶,描繪一群想逃避朽壞卻無處可逃的人。
10篇關於深邃的綠,原始的氣息,以及綠裡的諸多傳奇。
〈心愛的蘭花孩兒〉10篇關於深邃的綠,原始的氣息,以及綠裡的諸多傳奇。
在一片哀號中,他並不顯得特別突出,從山頂走回來身心經過一次洗滌,他覺得可以原諒一切,但是每當黃昏到來,他的背脊好似有蟻群在爬,熱癢難過,他就像一列脫軌的火車,斜倒在地,跟這個世界錯位挪移。
〈綠斗蓬〉
院子裡那對母子很沉默,幾乎不對談,卻極有默契,一個拿著鋤頭鋤草,一個撒培養土,有時少年附在母親耳邊低語,原來她幾乎聽不見,他們好像不屬於這世界,從心靈的一角剪下來的。
〈最後的櫻木花道〉
他們穿越能高古道,從霧社上山,在中央山脈能高鞍部一帶搜索,一直往花蓮的方向仔細尋找,沿途風景清奇美絕,古棧道與木造山屋充滿古意,清晨的山鑾被雲海環繞,恍如仙山,怪不得泰雅相信山靈。
〈然後然後〉
這輛188號公車往山上開,是很冷僻的路線,連她都沒搭過。她喜歡搭公車,沒固定目標,就是隨便搭,尤其是蹺課天,然後搭到終點站,這世上真有所謂終點站?終點之後是什麼呢?會不會是另一個起點?
〈紅咖哩黃咖哩〉
母親閉上眼睛,快速流下兩行淚,沒想到老輩的感情是這麼深沉,那是一個深沉的年代,像一座座火山口,流動著像百萬朵食人花瑰麗的熔岩,令人怕靠近,怕自己一靠近會縱身跳入。
作者介紹
作者簡介
周芬伶
政大中文系畢業,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,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。曾獲吳濁流小說獎、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。跨足多種創作形式,著有散文《紫蓮之歌》、《母系銀河》、《汝色》、《花房之歌》、《雜種》、《蘭花辭》、《北印度書簡》等,小說《影子情人》、《浪子駭女》等,以及少年小說、文學論著等多種,另編有散文、小說選本。
周芬伶
政大中文系畢業,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,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。曾獲吳濁流小說獎、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。跨足多種創作形式,著有散文《紫蓮之歌》、《母系銀河》、《汝色》、《花房之歌》、《雜種》、《蘭花辭》、《北印度書簡》等,小說《影子情人》、《浪子駭女》等,以及少年小說、文學論著等多種,另編有散文、小說選本。
序
自序
可怕的美
住在大度山已有六年,剛來時配到的房子一片廢墟,裡外整治約一年才能住人,山裡的生活與世隔絕,每天要面對毒蛇、虎頭蜂、蜈蚣、老鼠、白蟻入侵等等情節,白蟻常數日之間讓樹倒塌,屋樑地板朽壞,稍不小心,朽壞馬上降臨,獨居更加深這種無助感,對抗著這無所不在的朽壞,只能稍稍阻擋,然後隨遇而不安,這種不安感始終存在——我的鄰居因被虎頭蜂攻擊,心臟病發暴斃;才剛華麗裝修宿舍的另一個鄰居,令人讚歎的甜美草皮剛鋪好,他卻發覺自己癌末,不久去世,房子隨之失去光彩,草皮被雜草掩蓋,每回路過總感覺悲涼;不幸與災難來得如此蒼促,人力如此微弱,我也曾被蜜蜂叮得滿頭包,被毒蛇嚇到不敢回家,在這裡小小的事都會變成災難,有一次蟲殼飛進眼睛,痛到掛急診;出門一個不慎腳插進水溝,仰倒在草地上,直面藍天,我感到暈眩,並覺得天空如鍋蓋壓在我身上,我想罵髒話,眼淚卻自動到來。
但我喜歡山、樹林,各種花草,這是無可逆轉的,也許血液中有著山裡人的因子,令我想起住在叢林中過著原野生活,喜歡打獵的外祖父,九歲時曾與他住過一段時間,夜裡無燈,每日汲取河水放進黑色大水缸泡明礬過濾,那缸水是一天內煮飯與洗衣洗浴用水,得非常節約使用,大蜥蜴與毒蛇穿梭林間,而我們在溪河中泅泳,只為撈一些河蜆,那就是我們的食物,蚊子叮得我寫求救信,拜託母親救我回家,還好沒有,日後想起卻是懷念的日子。
我也想起我所來自的家鄉,地處北大武山下,鄰近都是原民區與客家庄,我們那個小鎮是少數的閩南人,移民兩三百年,常與原住民通婚,也許我們早已是原民化的山人,而自己竟不自知。潮洲離排灣聚集的農場、來義、泰武只有數公里,山民常頂著竹簍徒步到我家以物易物;我們則上山找同學,他們大多有好歌喉與很酷的名字,有個女孩叫夏玫瑰,聽說是公主。
因地處山腳,遍布原始森林,從小我就愛往林子裡鑽,那深邃的綠,原始的氣息,那綠裡有著許多傳奇,從民國九十七年起很自然地寫山民的生活,也沒多想,就是往那綠裡鑽,五年來陸續寫了十三篇,淘汰三篇,如果再多看幾眼,可能沒勇氣出版。
然這本書作為生命的本色,描寫的與其說是朽壞的人,不如說是那些想逃避朽壞而無處可逃的人。
山裡人是隨順自然,無處可逃之人,他們到山下只會更想念山上,所以面對一切天命與違逆忍受力超強,八八水災毀了霧台村,百合族裔魯凱被迫遷到山腰排灣區,許多人無法適應又返回祖地,我曾在那裡住過,滿山遍野的百合花與圖飾,在山之巔有條古道,山人就從這裡走到台東或花蓮,有多少的山村被洪水與地震吞沒,然而只要住過山上就會想再回去,這是山裡人的命運。
海拔三千,是人體還能忍受的高度,今年去了一趟喜馬拉雅山,海拔四千到七千,到那裡生活已超過一般人體極限,連官覺都會改變,慾望消減,心靈純淨,怪不得成為宗教聖地與香巴拉,那是另一種超現實,我無法補捉那超塵絕俗之美,只能描摹海拔三千以下的綠,那豐沛的綠,似乎是充滿慾望與想像的叢林,還有著眼耳鼻舌身意,還有塵垢,還有無明,只要無明存在,所有的恐怖顛倒夢想依舊存在。
超脫說起來容易,在現實中如何困難。
當散文中的小我寫煩了,抽離自己去看遠方的人——遠方的人對我恆常存在魅惑力,去抓住那些幻影,當作遠方的旅行,當我一次又一次歸來,常有如黃粱夢醒般清澈。
台灣是個海島,有關海已寫得很多,然而台灣同時是山國,百分之七十的高山,百座以上三千公尺高峰,那裡清麗脫俗,我曾縱走能高越嶺,六天五夜過棧道攀岩走壁,走到脫落四個腳趾甲,橫越台灣中部高山,山中的夜晚奇寒,嶺上結著霜,清晨的山頂雲霧與與群山好像在旋轉,在這裡樹變少,山變小,人失去存在感,我無法說明那山憾人的力量,它幾十年來跟隨著我,始終沒離去。
把它們看作山中傳奇也好,或是某種山的素描,我沒用力也沒花招,只是素樸地記錄山的記憶。
寫小說的我與寫散文的我越來越不同,以前它們或有交錯或交織,現在越離越遠,寫小說是遠方的旅行,向人訴說旅途的經歷,然而寫散文先要存在一個散文家,散文是散文家的文體,我是寫了十幾二十年,才有散文作者的鮮明意識,而小說是否也是小說家的文體,先存在著小說家,才有小說這回事?
最早的小說家是個說故事的人,他們行走四方以說故事娛樂大眾;當聽的故事變成寫定的小說,其中的小說家變成摹擬的人,如亞里斯多德所說,他們摹擬自然,自然包含神祇,他們同時是發現者,其時的悲劇多是命運悲劇,發現天命即是命運逆轉直下之時,如梅迪亞、安蒂岡妮,她們作出不得已的選擇,走向毀人或自毀之路;之後是性格悲劇,人的不幸來自自身的性格缺陷,如莎劇中李爾王的軟耳根及愛聽讒言;哈姆雷特的多疑軟弱,英雄的心通常破了個大洞;直至科學家發現遺傳與進化論,小說描寫的多是境遇悲劇,人的不幸是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環境構成,如包法利夫人、娜娜,她們的墮落是一步錯一步;至二十世紀初,小說描寫的多為心靈悲劇,如同《推銷員之死》中的老銷員,他先死於心靈,後死於自殺。當人對於不幸不但無力反擊,反而坐以待斃,這種悲哀無寧更為絕望。
現代小說多是憂鬱的,盧卡奇認為現代小說只是史詩的殘餘,故而主角都是憂鬱的流浪者,他們不是傻子、瘋子就是罪犯。然而小說家在不在其內呢?或者那個小說家根本是非人或超人。
史詩之後的小說家,從與魔鬼交易的天才到背負使命的良心導師,然後是召魂者或降靈師,最後是將垃圾變成黃金的打包工,然誰具有鑽石孔眼,把孤獨化為喧囂呢?
我是很願意當文學的打包工,從寫小說以來,圍繞著一主題而書寫,形成較大的架構,這種模式是有長篇的企圖,然尚無結構力,我把希望寄託在《花東婦好》,已寫近十年,這麼久了,再久一些無妨,《龍瑛宗傳》寫了近二十年才完工,我是從不急的。葉慈在〈一九一六年復活節〉寫著:
不管已說了和做了什麼。
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夢;
知道他們夢想過和已死去
就夠了;何必管過多的愛
在死以前使他們迷亂?
我用詩把它們寫出來——
麥克多納和康諾利,
皮爾斯和麥克布萊,
現在和將來,無論在哪裡
只要有綠色在表層,
是變了,徹底地變了:
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。
一種可怕的美快要誕生,急什麼呢?我沒有鑽石孔眼,只願像清晨小草上的露珠平和謙卑地照射。
可怕的美
住在大度山已有六年,剛來時配到的房子一片廢墟,裡外整治約一年才能住人,山裡的生活與世隔絕,每天要面對毒蛇、虎頭蜂、蜈蚣、老鼠、白蟻入侵等等情節,白蟻常數日之間讓樹倒塌,屋樑地板朽壞,稍不小心,朽壞馬上降臨,獨居更加深這種無助感,對抗著這無所不在的朽壞,只能稍稍阻擋,然後隨遇而不安,這種不安感始終存在——我的鄰居因被虎頭蜂攻擊,心臟病發暴斃;才剛華麗裝修宿舍的另一個鄰居,令人讚歎的甜美草皮剛鋪好,他卻發覺自己癌末,不久去世,房子隨之失去光彩,草皮被雜草掩蓋,每回路過總感覺悲涼;不幸與災難來得如此蒼促,人力如此微弱,我也曾被蜜蜂叮得滿頭包,被毒蛇嚇到不敢回家,在這裡小小的事都會變成災難,有一次蟲殼飛進眼睛,痛到掛急診;出門一個不慎腳插進水溝,仰倒在草地上,直面藍天,我感到暈眩,並覺得天空如鍋蓋壓在我身上,我想罵髒話,眼淚卻自動到來。
但我喜歡山、樹林,各種花草,這是無可逆轉的,也許血液中有著山裡人的因子,令我想起住在叢林中過著原野生活,喜歡打獵的外祖父,九歲時曾與他住過一段時間,夜裡無燈,每日汲取河水放進黑色大水缸泡明礬過濾,那缸水是一天內煮飯與洗衣洗浴用水,得非常節約使用,大蜥蜴與毒蛇穿梭林間,而我們在溪河中泅泳,只為撈一些河蜆,那就是我們的食物,蚊子叮得我寫求救信,拜託母親救我回家,還好沒有,日後想起卻是懷念的日子。
我也想起我所來自的家鄉,地處北大武山下,鄰近都是原民區與客家庄,我們那個小鎮是少數的閩南人,移民兩三百年,常與原住民通婚,也許我們早已是原民化的山人,而自己竟不自知。潮洲離排灣聚集的農場、來義、泰武只有數公里,山民常頂著竹簍徒步到我家以物易物;我們則上山找同學,他們大多有好歌喉與很酷的名字,有個女孩叫夏玫瑰,聽說是公主。
因地處山腳,遍布原始森林,從小我就愛往林子裡鑽,那深邃的綠,原始的氣息,那綠裡有著許多傳奇,從民國九十七年起很自然地寫山民的生活,也沒多想,就是往那綠裡鑽,五年來陸續寫了十三篇,淘汰三篇,如果再多看幾眼,可能沒勇氣出版。
然這本書作為生命的本色,描寫的與其說是朽壞的人,不如說是那些想逃避朽壞而無處可逃的人。
山裡人是隨順自然,無處可逃之人,他們到山下只會更想念山上,所以面對一切天命與違逆忍受力超強,八八水災毀了霧台村,百合族裔魯凱被迫遷到山腰排灣區,許多人無法適應又返回祖地,我曾在那裡住過,滿山遍野的百合花與圖飾,在山之巔有條古道,山人就從這裡走到台東或花蓮,有多少的山村被洪水與地震吞沒,然而只要住過山上就會想再回去,這是山裡人的命運。
海拔三千,是人體還能忍受的高度,今年去了一趟喜馬拉雅山,海拔四千到七千,到那裡生活已超過一般人體極限,連官覺都會改變,慾望消減,心靈純淨,怪不得成為宗教聖地與香巴拉,那是另一種超現實,我無法補捉那超塵絕俗之美,只能描摹海拔三千以下的綠,那豐沛的綠,似乎是充滿慾望與想像的叢林,還有著眼耳鼻舌身意,還有塵垢,還有無明,只要無明存在,所有的恐怖顛倒夢想依舊存在。
超脫說起來容易,在現實中如何困難。
當散文中的小我寫煩了,抽離自己去看遠方的人——遠方的人對我恆常存在魅惑力,去抓住那些幻影,當作遠方的旅行,當我一次又一次歸來,常有如黃粱夢醒般清澈。
台灣是個海島,有關海已寫得很多,然而台灣同時是山國,百分之七十的高山,百座以上三千公尺高峰,那裡清麗脫俗,我曾縱走能高越嶺,六天五夜過棧道攀岩走壁,走到脫落四個腳趾甲,橫越台灣中部高山,山中的夜晚奇寒,嶺上結著霜,清晨的山頂雲霧與與群山好像在旋轉,在這裡樹變少,山變小,人失去存在感,我無法說明那山憾人的力量,它幾十年來跟隨著我,始終沒離去。
把它們看作山中傳奇也好,或是某種山的素描,我沒用力也沒花招,只是素樸地記錄山的記憶。
寫小說的我與寫散文的我越來越不同,以前它們或有交錯或交織,現在越離越遠,寫小說是遠方的旅行,向人訴說旅途的經歷,然而寫散文先要存在一個散文家,散文是散文家的文體,我是寫了十幾二十年,才有散文作者的鮮明意識,而小說是否也是小說家的文體,先存在著小說家,才有小說這回事?
最早的小說家是個說故事的人,他們行走四方以說故事娛樂大眾;當聽的故事變成寫定的小說,其中的小說家變成摹擬的人,如亞里斯多德所說,他們摹擬自然,自然包含神祇,他們同時是發現者,其時的悲劇多是命運悲劇,發現天命即是命運逆轉直下之時,如梅迪亞、安蒂岡妮,她們作出不得已的選擇,走向毀人或自毀之路;之後是性格悲劇,人的不幸來自自身的性格缺陷,如莎劇中李爾王的軟耳根及愛聽讒言;哈姆雷特的多疑軟弱,英雄的心通常破了個大洞;直至科學家發現遺傳與進化論,小說描寫的多是境遇悲劇,人的不幸是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環境構成,如包法利夫人、娜娜,她們的墮落是一步錯一步;至二十世紀初,小說描寫的多為心靈悲劇,如同《推銷員之死》中的老銷員,他先死於心靈,後死於自殺。當人對於不幸不但無力反擊,反而坐以待斃,這種悲哀無寧更為絕望。
現代小說多是憂鬱的,盧卡奇認為現代小說只是史詩的殘餘,故而主角都是憂鬱的流浪者,他們不是傻子、瘋子就是罪犯。然而小說家在不在其內呢?或者那個小說家根本是非人或超人。
史詩之後的小說家,從與魔鬼交易的天才到背負使命的良心導師,然後是召魂者或降靈師,最後是將垃圾變成黃金的打包工,然誰具有鑽石孔眼,把孤獨化為喧囂呢?
我是很願意當文學的打包工,從寫小說以來,圍繞著一主題而書寫,形成較大的架構,這種模式是有長篇的企圖,然尚無結構力,我把希望寄託在《花東婦好》,已寫近十年,這麼久了,再久一些無妨,《龍瑛宗傳》寫了近二十年才完工,我是從不急的。葉慈在〈一九一六年復活節〉寫著:
不管已說了和做了什麼。
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夢;
知道他們夢想過和已死去
就夠了;何必管過多的愛
在死以前使他們迷亂?
我用詩把它們寫出來——
麥克多納和康諾利,
皮爾斯和麥克布萊,
現在和將來,無論在哪裡
只要有綠色在表層,
是變了,徹底地變了:
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。
一種可怕的美快要誕生,急什麼呢?我沒有鑽石孔眼,只願像清晨小草上的露珠平和謙卑地照射。
文章標籤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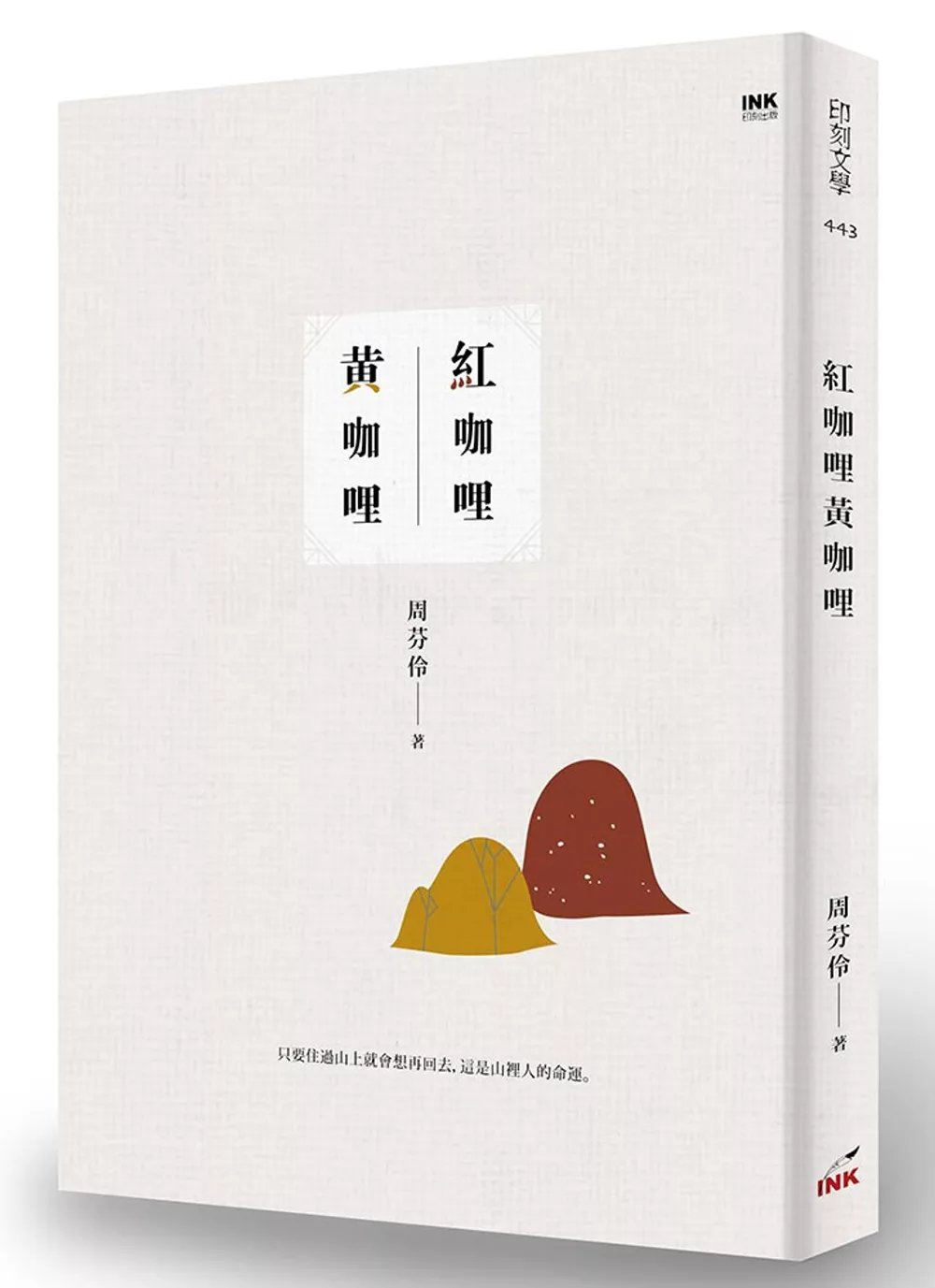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